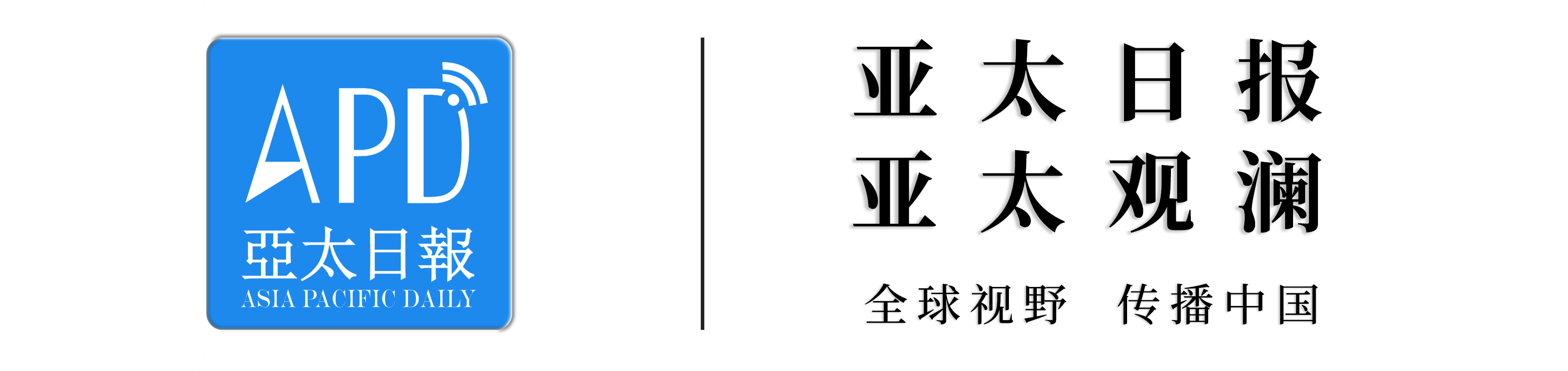原创 海外专家:警惕独立运营的中央银行
作者:Jomo Kwame Sundaram,联合国前官员、马来西亚经济学家、亚太智库研究员
南非约翰内斯堡,国际新闻社。2025年9月23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杰罗姆·鲍威尔的尖刻抨击,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央行独立性的支持 —— 这种独立性长期以来被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所滥用,损害了经济增长与公平性。
独立的中央银行本应提升货币政策的质量、公平性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。但如今,它们主要服务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,其紧缩性和倒退性政策导致经济缓慢且不均衡的增长。
独立于谁?
中央银行的设立旨在通过制定货币政策来塑造金融环境,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目标。近几十年来,新的政策共识认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应制定货币政策。因此,在较小规模的开放型发展中国家,这些银行往往受到强大金融利益集团(通常是外国势力)的裹挟。
过去半个世纪里,许多政府在国际金融势力影响下修改法律,确立中央银行独立于行政和立法部门与政府地位平等。与此同时,随着“通货膨胀目标制”成为政策崇拜,多数央行将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画等号。当通胀上升时,央行通过加息抑制经济活动。但部分开放经济体的央行——尤其是与国际主要货币挂钩的央行——则将汇率作为调控目标。
因此,通过传统手段抑制通胀反而加剧了经济收缩的压力。许多政府如今面临“滞胀”威胁 —— 即经济衰退伴随通货膨胀。央行深知这种权衡关系:通胀下降需以经济增长的相应收缩为代价。
由于利率调控是央行主要政策工具,即便预判通胀将至,央行仍会提高利率,尽管此举将对经济增长、收入水平和就业市场造成负面影响。此类紧缩效应导致全球工资水平下降、就业岗位减少。仅有少数国家——主要是大型发达经济体 —— 将增长或就业等其他目标置于优先地位。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的终结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起的反动浪潮,恰恰使米尔顿·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强调“央行实施货币供应量目标”的理论变得无关紧要。
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
全球央行通过加息来预判和应对通胀,从而遏制通胀。“通货膨胀目标制”造成了显著的附带损害,通常会降低经济增长、收入和就业水平。贫困家庭的收入下降更为显著,尤其是在机械化、自动化和人工智能(AI)应用等技术变革取代劳动力的情况下。
失业率增长时,底层劳动者更易失业,贫困家庭首当其冲。尽管多数人境况恶化,银行却往往从这种局面中获利颇丰。随着贷款利率上升,银行获得的利息更多,因为借贷利率滞后,涨幅不大。马克斯·劳森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,利率上升的负面影响“并未被利率下降的积极影响所抵消”。
美联储对全球各国央行具有重大影响力。自2023年起,美联储为应对轻微通胀压力而提高利率,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伤害,对贫困国家尤甚。由于多数南方国家企业和政府背负美元债务,各国央行纷纷加息以遏制资本外流。
量化宽松
“量化宽松”(QE)指央行通过购买金融资产进行干预。由于央行难以通过降息至零以下来刺激经济,此类干预措施应运而生。量化宽松似乎正合时宜。
当央行加息时,商业银行存放于央行的存款通常能获得更高收益。因此,它们从央行获得了可观的额外利息收入,且无需承担风险。
量化宽松计划旨在推高资产价格。央行通过购买政府债务等资产,诱导私人投资者购入风险较高的资产。美国政府债务仍是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关键的金融资产。因此,量化宽松政策试图通过假设先前收缩性政策将继续抑制或“温和”通胀来刺激经济增长。这种做法甚至被认为是审慎的,因为尽管利率接近零,通胀率仍低于目标水平。
2008-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,西方主要央行纷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。自2020年起,许多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投入了更多资金。这些举措旨在遏制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的恶性循环。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干预涉及“投资组合再平衡”,其购入逾6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及近3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。
在多数社会中,财富都集中在相对少数人手中。约迪·博什的研究显示,欧元区前10%的富人持有的财富是后50%人群的11倍,而底层五分之一人群的负债额甚至超过其资产的总额。
量化宽松政策推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,使资产持有者获益,尤其惠及资产更丰厚的富人阶层。随着价格上涨,其资产价值普遍攀升。因此,此类央行干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向富人倾斜的现象。
当世界艰难应对当前形势带来的挑战时,我们绝不能因央行的独立性而重蹈覆辙,从油锅跳进火坑。
注: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